中法两大文明,无论是追溯历史,还是就现实而论,都是人类最富有创造性的宝藏。而法国朋友,则是我们了解法国文明的重要桥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常驻法国的20多年间也的的确确从诸多法国朋友那里获得大量精神果实。而这些果实,又通过我的笔,传播给我的同胞们。反过来,我也通过这些法国朋友,将涉及中国的信息——特别是客观的、正面的信息——传递出去,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中国。如此,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理解,加强了双方的友谊和感情,这就是文化交流的深层次意义。
常年关注我有关法国报道的读者肯定也会注意到,在常驻法国的第二个十年里,我也开始向法国、向海外舆论圈来谈——中国!当时正值我们开始致力于建立文化自信,为了让别人认识我们,我便在法国媒体上撰文发声,介绍中国。除了在报刊上、在电视电台里谈论中国外,我还直接用法语撰写了《与你一样的中国人》(Les Chinois sont des hommes comme les autres)一书,并在法国出版,以详尽地告诉世人,中国人是谁,从何而来,欲往何处去。
谈到这本书,我就不能不谈到我的两位法国挚友:马尔萨尔(Marcel Marsal)和雷诺·德罗什布伦(Renaud de Rochebrune)。
我是通过法国著名新闻周刊《青年非洲》结识雷诺的。那是本世纪初,中国发展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青年非洲》作为一份主要在非洲发行的法国刊物,当然也不例外。而雷诺是《青年非洲》地位相当特殊的合作者。每次编辑部会议,当众人意见不一时,其创始人、周刊社长本·亚美德(Béchir Ben Yahmed)就会转向雷诺:“你呢?雷诺,你怎么想?”雷诺不但很有主见,而且才华出众,他总能想出一些高招儿,来解决周刊遇到的各类难题。当时编辑部同事七嘴八舌出了不少主意,有的说要请法国驻华记者来写,有的说要请汉学家来露一手,而雷诺则说出了一句令众人一致赞同的话:“为什么不找一位中国人来写他自己的国家呢?”因为《青年非洲》的媒体人都知道,非洲读者不同于欧洲读者,他们普遍对中国有好感,而一些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可真是谈不上客观友好。

雷诺·德罗什布伦
说起来,雷诺还真是通过一贯持反华立场的法国汉学家玛丽·霍尔兹曼(Marie Holzman)找到我的。霍尔兹曼与我在诸多场合公开辩论过有关中国的问题,我们算是“不打不相识”。而雷诺当时对中国的看法,坦率地讲,也与霍尔兹曼没有太大差异。但他还是明确表示,必须请一位来自中国的记者谈中国。很快,《青年非洲》上出现了一位署名“Yi Chen”的记者,专门报道中国。他的文章非常受非洲读者的欢迎。这个“逸尘”就是我。当时我的法语水平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我对非洲读者的“中国观”也很陌生,更何况这只是我的业余写作。雷诺耐心地为我寻找主题、修改稿件,甚至帮我回复读者来信。当我的稿件在编辑部遭到一些对中国怀有偏见的记者编辑们反对时,雷诺经常力挽狂澜,坚持要刊登我的文章。随着后来青年非洲媒体集团创刊针对法国读者的月刊《杂志》(La Revue),我又在雷诺的推荐下成为该刊的特约撰稿人。这份月刊的对华报道当时在法国独树一帜,具有一定的影响。
雷诺并不是一个亲华人士,为什么他愿意支持一名中国记者对法、非读者报道中国呢?这是因为在法国的媒体中,确实存在着一批希望客观、公正、自由地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媒体人,而雷诺就是其中一员。
从媒体的角度来看,雷诺并不认同目前西方的舆论格局。比如对法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他历来就嗤之以鼻。雷诺年轻时可谓走遍天下,比如印度、日本、新加坡等,他都去过。“我过去对中国的认识几乎全部源于西方媒体,我知道那是不全面的,是有偏颇的。但我听不到中国人自己的声音……”雷诺认识我后曾这样说过。所以,他全力支持我在法国媒体上发声。
雷诺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撰写、出版的有关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关系史的书籍已经成为经典。他同时也是一位书刊编辑,在老牌出版社德诺埃尔(Denoël)担任主编。正是他,在与我合作几年后,直言建议我用法语撰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一本不同于在法国能够看到的其他类型的涉及中国的书。当时在法国,有关中国的书非常多,但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划归“反华类型”的。要写这样一本书,我作为一个中国作者,即使有压力,也是很正常的。但雷诺作为主导这本书出版工作的主编,他承受的压力才是真正可怕的。但雷诺毫无惧色,因为他认准了我写的东西是能够经受现实和历史考验的。
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却惺惺相惜,彼此欣赏。我们经常共进午餐,一起喝咖啡,目的都是对我们观察到的国际事务进行讨论。雷诺曾是一位深受“五月风暴”(1968年5月在法国爆发的一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影响的激进青年,生活极其简朴,漠视名利,酷爱自行车运动。他性格极其倔强,但同时又抱持坚定的核心理念——即真理、平等和自由等思想。
我最为骄傲的一点,就是让雷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深刻变化,更接近于中国现实。认识我之前,他很少写中国。但随着我们对中国的讨论日益深入,他逐渐理解了中国革命,理解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他开始在《杂志》月刊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评论,从他的独特角度,向法国、非洲读者介绍一个他所理解的中国。当我的《与你一样的中国人》出版后,法国多家媒体发表了书评,电视台也邀请我去谈我的书。他非常高兴。
雷诺总是跟我说,作为一名记者,他没有别的野心,就是想向读者传递一个真实的世界。从雷诺身上,我体会到的是坚持追寻真理、真相的一代法国人。尽管法国有一股反华势力在舆论圈蓄意地诋毁、贬低中国,但也确实存在着一批拒绝盲目追随他们,坚定要求寻求真相、寻求真理的记者。我欣赏他们,钦佩他们。同时我也体会到,由于长期处于早已形成的媒体对华虚构的负面印象的包围之中,他们很难看到真实的中国。所以,我们必须突破这种思想包围,与他们直接接触,与更多的人交朋友。
回国后,我和雷诺就逐渐失去了联系。不久前我刚刚获悉,他于前年9月22日突然无恙逝世,享年75岁。我深为伤感、悲哀。
雷诺的离去,使我产生了一种紧迫感,我开始试着与法国老朋友们恢复联系。就在这当口,老朋友多米尼克·布隆贝尔热(Dominique Bromberger)从法国来电话问候我。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毕竟他可是一位名扬法国的“名记”——他当年出车祸后,希拉克总统曾亲自致电慰问。法国《巴黎竞赛画报》曾这样报道过他:这是一位永远只戴领结、不碰领带的绅士,他的领结已经成为他的一个标志。

多米尼克·布隆贝尔热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刚到法国担任常驻记者不久,在一次随法国时任总统前往马斯特里赫特参加欧盟峰会的专机上,布隆贝尔热恰好坐在我身边。作为当时随法国总统访问过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法国媒体人,这位“名记”挺愿意与一位中国记者——当时在法国属于“稀有品种”——聊聊天。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布隆贝尔热对法国政坛和新闻界的种种内幕可谓了如指掌。正是通过他,我也逐渐了解到法国鲜为人知的一面。在马斯特里赫特峰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当时布隆贝尔热坐在记者席第一排,记者会一开始,他就举起手要求提问。但近在咫尺的总统就像看不见他似的,就是对他不理不睬。当时,这一幕曾引起法国多家媒体的大肆报道。
我们成为好朋友后,布隆贝尔热将当时的内幕悄悄地告诉了我。原来,当时的法国总理(由总统任命)曾到布隆贝尔热供职的法国电视一台(TF1)接受采访。这家电视台在私有化之后,被布依格房地产公司收入囊中。而布依格房产公司在这位总理当财政部长的时候,就与他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从政府那里得到过多个公共项目。当时,总理正身陷经济丑闻的漩涡之中,媒体揭露他从一位大资本家手中“借”了100万法郎,有借据,却拿不出已经还钱的证明。因此,媒体正盯着他穷追不舍呢。他需要到媒体上谈政府新政,之所以专门选择TF1,就是出于与该台老板布依格有着密切私交的考虑。布隆贝尔热当时是TF1晚间新闻节目的主持人。果然,在节目采访前,TF1老板就特意关照布隆贝尔热,要“提好问题”。在法国,新闻是“自由”的,谁也不能规定记者问什么不问什么,但提醒你要“提好问题”当然是有潜台词的。布隆贝尔热自然也是心中有数,但问不问借钱一事,这明显涉及一名记者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最终,布隆贝尔热没有忍住,在节目最后一分钟还是轻轻问了一句:“你到底还了钱没有?”总理顿时勃然大怒……
从此,法国政府便开始给布隆贝尔热冷板凳。上述他在记者会上被总统冷落的一幕就是一个例子。更关键的是,TF1老板布依格也立马开始排斥他。一年后,布隆贝尔热不得不从TF1辞职走人。他后来曾到多家其他电视台如ARTE(德法公共电视台)等供职,但哪家电视台的影响力都比不上TF1,特别是晚间新闻节目。他的职业生涯从此开始走向下坡路。
法国媒体和政府的关系就是这样既密切、又相互制约。而当两者遇到其背后的财团(即资本)的时候,便立即露出其软肋……由此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真正的所谓“三权分立”,其实是指政府、媒体和资本。应该坦承,我从布隆贝尔热处得到很多这类“新闻”,因为他实在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消息灵通人士”。
今天,八十高寿的布隆贝尔热已出版多部著作,其中有一本是写俄罗斯的,题为《就是这样的,俄罗斯》(C’est ça, la Russie)。我曾调侃地问他,什么时候也来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他说:“好啊,等我再去中国看看……”中国欢迎你,多米尼克!
在我的法国朋友中,懂中文的不多。魏柳南是其中一位。他的法文名字叫Lionel Vairon,“魏柳南”是他自取的中文名。他是与他的半华裔的妻子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起到中国台湾学的中文。懂中文的法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台湾学的,他们往往在政治上也会受到台湾的影响。但魏柳南却是一个绝对的例外,他一直对中国大陆非常向往:一是他的政治观点明显是左翼的,对社会主义中国怀有一定的好感;二是他与非洲、阿拉伯等发展中国家联系非常广泛,他一直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中国与这类国家之间的纽带。

2005年2月,郑若麟(右)陪同魏柳南(中)访问新疆期间在火焰山合影。
从大学毕业拿到博士学位后,魏柳南先是进入媒体成为记者,后转入法国外交部成为职业外交官,后来又因政治因素而辞职,创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开始致力于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的联络。
尽管会讲中文,但他此前却一直与中国“无缘”。说起来,他第一次访华还是我促成的。那是2005年,魏柳南多次接受《文汇报》采访,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关注。于是,报社便邀请他前来中国,由我陪着他从上海跑到新疆等多地。我清楚地记得,他对火焰山等风景名胜并没有太大兴趣,但对新疆书店里用各种民族语言出版的书籍却问之又问,还拍了很多照片。他说,这个细节是对法国媒体说“中国对少数民族进行文化种族灭绝”的最有力反击。
那次访华之后,魏柳南对中国的喜欢便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三个月必来一次中国。他一共来了多少次,我没有统计过,但我知道他已经深刻地认识了中国。他曾对我说:“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向绝对代表着人类世界未来的愿景。我们法国、欧洲,特别是我努力服务的亚非拉国家,更是应该全面加强对华关系……”他是这么判断的,也是这么致力于行动的。他像很多热爱中国的法国朋友一样,为中法关系、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默默地做了很多工作。
作为一名学者,他笔耕不辍。他的一本《中国的挑战》(Défis chinois)是法国不可多得的深度客观分析中国对世界正面影响的专著。这本书不仅出版了中文版,而且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对传播真实的中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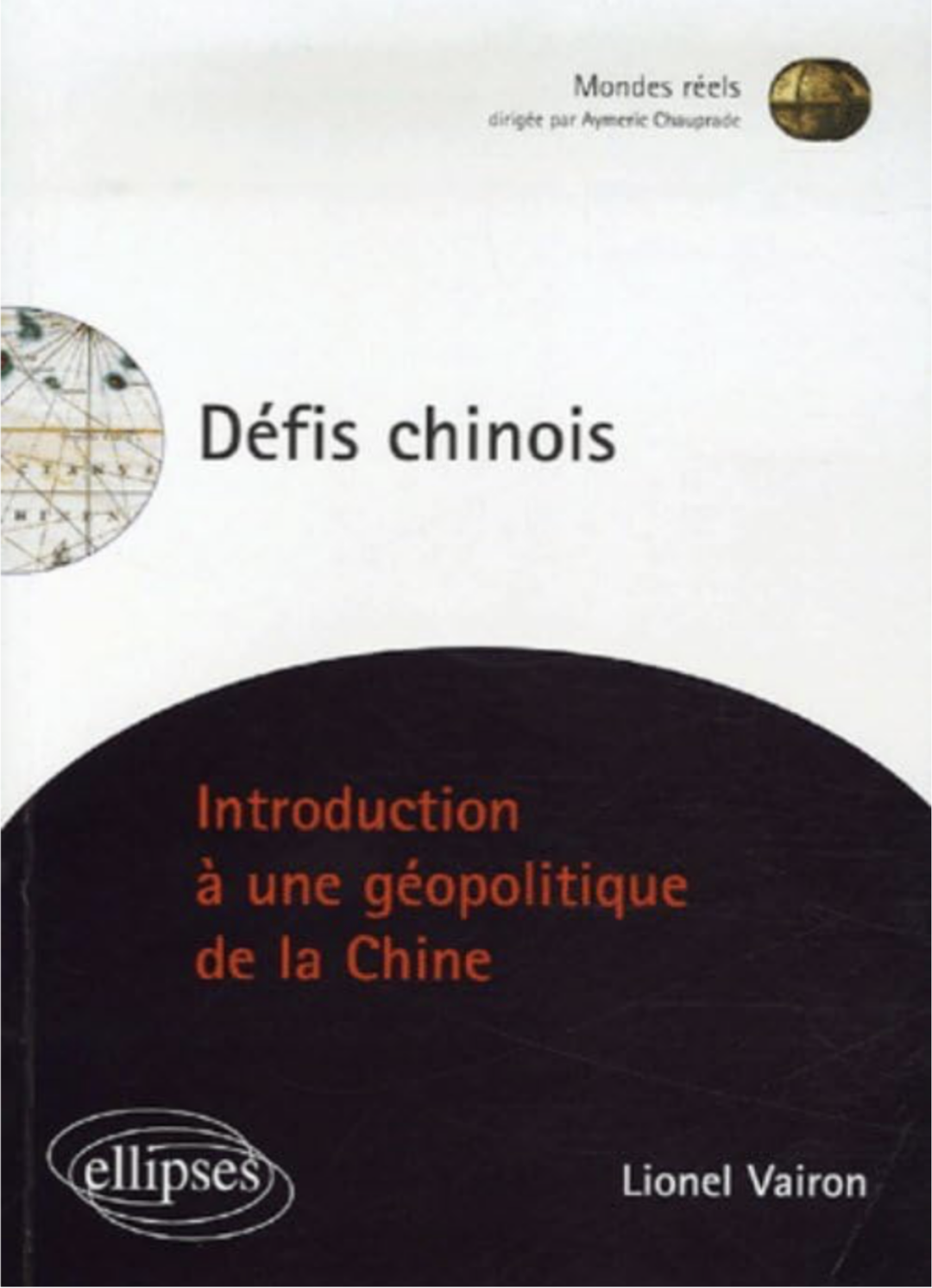
魏柳南《中国的挑战》法文版封面
令我极其难过的是,魏柳南刚到耳顺之年,就不幸身患绝症……他去世后,很多国人撰文深切悼念。魏柳南是一位中国真正的朋友,他的微笑永远会留在我们心间。
我的法国挚友还有很多。今天,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的心灵和友谊却是长存的。我们都坚信,在今天如此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下,各国普通民众之间真诚的友谊,才是世界和平的真正基石。
(作者:郑若麟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文汇报》前驻法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陶恒)

